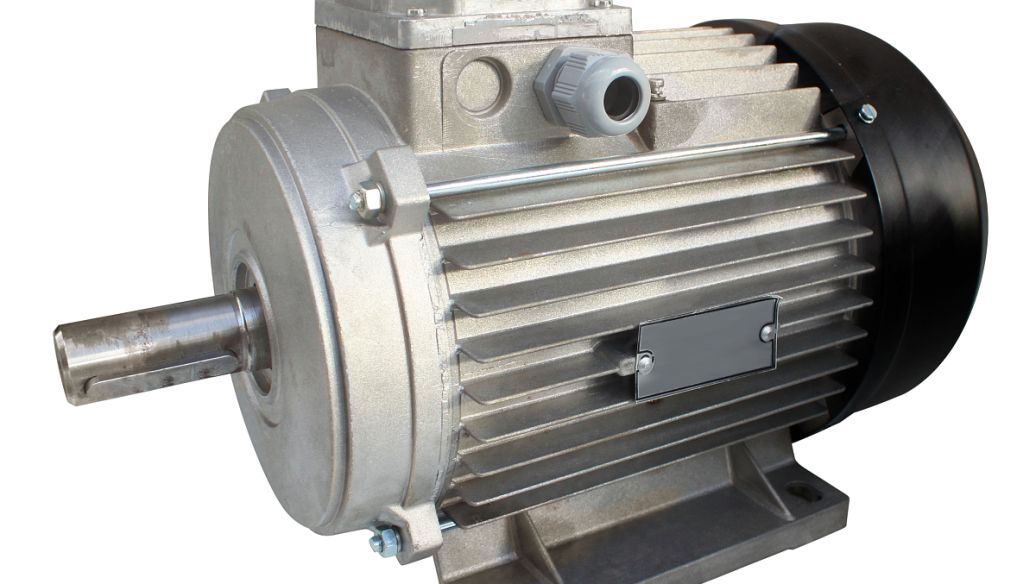听闻夫子去世,冉雍的笔停住。他的眼神停留在来人的脚踝处,甚至没有察觉笔管已从手中滑落,花了衣襟。
他撑着条案站起身来,沿着哭丧声去了孔子卧房。孔家人和学生跪了一地。冉雍看着榻上不再言语的枯骨,一阵眩晕,下意识地扶住墙。
“仲弓……”
有人叫住了他,他却没有回头,径直走出了那间屋子。回到自己的耳房,重新拿起了笔。
“仲弓,子华并不缺那些个粟米。”
那日他从公西赤家中回来,夫子正在房中读书,抬起头来笑着对他说。
冉雍一愣,与夫子对视半晌,方才深深一揖道:
“夫子说的是,雍识人不明。”
“无妨。”夫子摆了摆手,“给便给了,追究无益。”
“我给了她五秉。”
这次轮到夫子愣住。起先公西赤出使齐国,冉雍向夫子要粟米给公西赤的母亲。夫子说给一釜,他求夫子增加些,夫子也只说与其一庾。可他却自作主张,拿了五秉。
“雍啊,君子当救急,不当与富人锦上添花。”
夫子说完那句话,微微点了点头。冉雍低下头再拜,他感到夫子的眼神在他身上停留了许久。他知道公西赤将出使齐国,肥马轻裘不在话下,可他说不出为什么。他并不是那种喜欢与夫子争辩而标新立异的人,也不是颜渊那种乖顺的学生。与夫子的关系,他自己说不清楚。有时他们的意见南辕北辙,各有坚持,彼此却从未想过要分开。
早年他被聘为季氏家臣,收拾行装时,猛地抬头,发现夫子正站在他前面,默默地注视着他:
“你这是要老死在他家?”
冉雍思忖片刻,作揖拜下:
“在斯位而已。”
“去吧。”
夫子并未多言,转身离开。冉雍看着夫子的背影将要没入夜色,忽然觉得寂寥,忙道:
“学生请问仁!”
夫子回过头来,凝视着他,笑道:
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;在邦无怨,在家无怨。”
“雍,会照做的。”
夫子依旧笑着,轻轻摇了摇头。
不过三个月,冉雍便回来了。
“事情做得不顺心么?”夫子拍拍他的肩。
“不可谓不顺心,只是想回来。”
“回来吧,我养着你!”夫子哂笑道。
“夫子无怨?”
“求之不得。”
夫子去后,冉雍房中的灯连着亮了三夜。自有人置办丧事,而他只在意那人生时。眼前一黑,冉雍无力地倒在榻前。
雍也,可以使南面。
“夫子——!”冉雍发狠地奔跑,声嘶力竭地呼喊。夫子的身形近在眼前,却无法迫近。
跑了许久,发冠以散乱,袍裾也已丢弃在途中。染霜的长发纵横在汗涔涔的脸上和胸前,此外周身再无蔽体之物,宛若赤子一般。长时间的奔跑几乎令他窒息,终于倒在了道旁。
“夫子……”他抬起头,惊见夫子竟跪坐在他面前。
“丘,愿北面为臣。”夫子拜道。
(第一次写夫子同人,太嫩,见谅。)
他撑着条案站起身来,沿着哭丧声去了孔子卧房。孔家人和学生跪了一地。冉雍看着榻上不再言语的枯骨,一阵眩晕,下意识地扶住墙。
“仲弓……”
有人叫住了他,他却没有回头,径直走出了那间屋子。回到自己的耳房,重新拿起了笔。
“仲弓,子华并不缺那些个粟米。”
那日他从公西赤家中回来,夫子正在房中读书,抬起头来笑着对他说。
冉雍一愣,与夫子对视半晌,方才深深一揖道:
“夫子说的是,雍识人不明。”
“无妨。”夫子摆了摆手,“给便给了,追究无益。”
“我给了她五秉。”
这次轮到夫子愣住。起先公西赤出使齐国,冉雍向夫子要粟米给公西赤的母亲。夫子说给一釜,他求夫子增加些,夫子也只说与其一庾。可他却自作主张,拿了五秉。
“雍啊,君子当救急,不当与富人锦上添花。”
夫子说完那句话,微微点了点头。冉雍低下头再拜,他感到夫子的眼神在他身上停留了许久。他知道公西赤将出使齐国,肥马轻裘不在话下,可他说不出为什么。他并不是那种喜欢与夫子争辩而标新立异的人,也不是颜渊那种乖顺的学生。与夫子的关系,他自己说不清楚。有时他们的意见南辕北辙,各有坚持,彼此却从未想过要分开。
早年他被聘为季氏家臣,收拾行装时,猛地抬头,发现夫子正站在他前面,默默地注视着他:
“你这是要老死在他家?”
冉雍思忖片刻,作揖拜下:
“在斯位而已。”
“去吧。”
夫子并未多言,转身离开。冉雍看着夫子的背影将要没入夜色,忽然觉得寂寥,忙道:
“学生请问仁!”
夫子回过头来,凝视着他,笑道:
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;在邦无怨,在家无怨。”
“雍,会照做的。”
夫子依旧笑着,轻轻摇了摇头。
不过三个月,冉雍便回来了。
“事情做得不顺心么?”夫子拍拍他的肩。
“不可谓不顺心,只是想回来。”
“回来吧,我养着你!”夫子哂笑道。
“夫子无怨?”
“求之不得。”
夫子去后,冉雍房中的灯连着亮了三夜。自有人置办丧事,而他只在意那人生时。眼前一黑,冉雍无力地倒在榻前。
雍也,可以使南面。
“夫子——!”冉雍发狠地奔跑,声嘶力竭地呼喊。夫子的身形近在眼前,却无法迫近。
跑了许久,发冠以散乱,袍裾也已丢弃在途中。染霜的长发纵横在汗涔涔的脸上和胸前,此外周身再无蔽体之物,宛若赤子一般。长时间的奔跑几乎令他窒息,终于倒在了道旁。
“夫子……”他抬起头,惊见夫子竟跪坐在他面前。
“丘,愿北面为臣。”夫子拜道。
(第一次写夫子同人,太嫩,见谅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