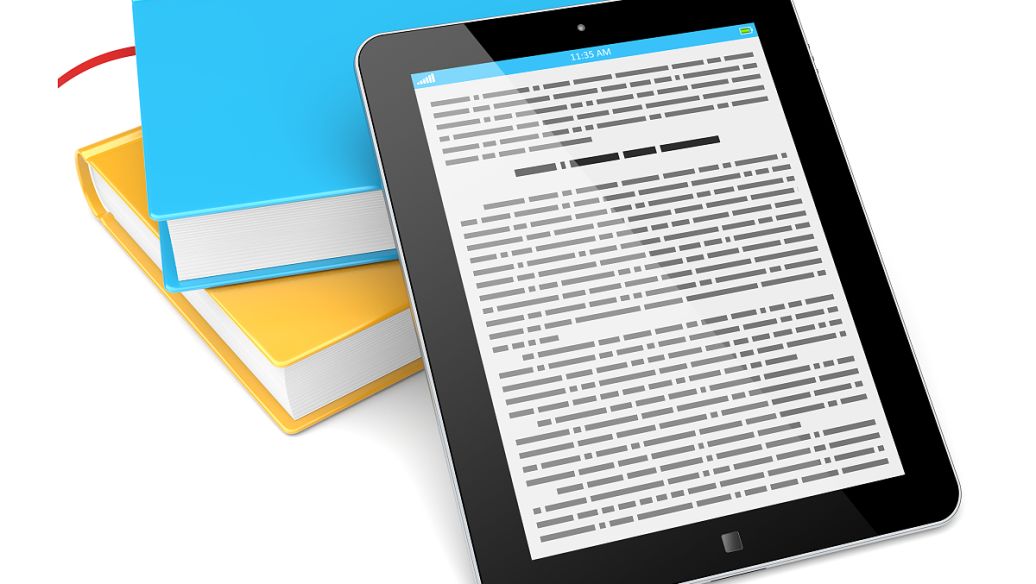离开医院以后的鸠山先是小跑了一会,到了人稍多的地方才慢下脚步。她怀着那种不安径直往前走,走到主街道的时候才在一家甜品屋门口的长椅上坐下,要了一杯加冰的糖水。夏日燥热时特有的一种音波一环一环的从上空荡漾下来,撞在自己的耳膜上,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声音。她盯着面前熙熙攘攘的人群,看见一张张被热气蒸得毫无生机的脸,有年轻的也有堆满皱纹的,高高低低的,从左边移过来的,被某座肩膀遮住了一瞬间后继续出现,消失在右边;从右边过来的,被左边过来的某撮发遮挡过后,已换了一副表情。
她手紧握着玻璃杯,空气中的水汽在剔透的玻璃上冷凝,像蚯蚓一样从杯的上端扭动着划到下端,反射着晃眼的光点。她干燥的手指被浸湿了。
随后她又买了切成小小方形的抹茶糕,每碟里面只有四块;又买了三色丸子,里面包裹了雪菊屋特制的夹心,撒了细碎得几乎同粉末的果仁。村子里的甜品屋不少,雪菊屋的质量和价格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她慢慢的品尝,一个丸子的滋味能让她回味很久,而更多的时间是在观察来来往往的路人和地面上的影子,当影子又开始拉长时,她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,这是她很多年来花钱花得最随心所欲的一次。
鸠山站起身往前走了几步,侧过头,若有若无的瞥了一眼甜品屋的屋顶。
她的住所在很偏的旧居民区,终年冷清清的,似乎住在那里的人都不愿出门,或是一出门就要走得远远的。她实在不愿意回去,但不得不回去一趟,于是她离开人群,拐过好几个弯,经过一棵特别高的樟树,走进了一条盘着山丘的斜巷。
她回到了自己的公寓,站在门口思忖了一会,把窗帘都拉上了,然后锁上门。光仍透过浅蓝色的窗帘布透了进来,只不过被削弱了好几层,苟延残喘地趴在边缘长了裂纹的餐桌上。她一边往浴室的方向走,一边随手将脱下来的衣服扔在地上。最后她像一条白鱼一样泡在浴缸里,水的冷意扒开燥热直浸到了她的骨子里。
也许是在外面灿烂的阳光里待太久了,浴室里的白炽灯格外昏暗。
屋子里只有滴答滴答的水声。
她闭着眼睛往后靠,先是双腿闭拢着抬出了水面,搭在浴缸的另一侧,再是抬起浸在水中的修长的手臂,水珠顺着肌肤滴下来撞击着水面,她弯曲的手指上赫然挂着一把水淋淋的苦无。她睁开眼。
带着狸猫面具,背着太刀的忍者站在自己面前。
意料之中的事。
她冷笑了一声,站起身,全身赤裸却毫无遮掩的站在了他面前。
他举起太刀,下一秒,殷红的血花溅落在了白色的瓷砖墙壁上,然后以不快不慢的速度滑下来,留下一道道长长的红痕,正像装着冰水的玻璃杯上冷凝的水珠流下来时的样子,只不过水珠是没有颜色的。
浴缸里的水被染红了,暗部忍者的尸块在里面一沉一浮。真纪将他脸上的面具揭下,看到他的表情定格在了惊恐的一瞬间。那是一张陌生的脸,于是她又把面具给他戴回去了。
就在刚刚,在她睁开眼的一瞬间,她的右眼发生了奇妙的变化,像是火一样的灼热,但是汇聚了一种说不明的力量,那种力量把她整个身体都充实起来了,让她心安。她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,好像根本什么都没做,就看见两道黑色的像刀刃一样的东西从自己面前划过,然后对方就变成了三截。
那个叫大蛇丸的人所说的话一股脑儿的涌了上来,她感到莫名兴奋——这不是咒印的力量,而大蛇丸说过让她注意自己的右眼,这也许就是他说过的独属于她自己的东西。
她站在浴缸旁边,用花洒冲走了地上和墙上的血迹,然后又仔细地清洗了自己的身体,闻着洗发水和沐浴露绵白的泡沫散发出的橄榄香——香味离得太近,盖住了那股血腥味。
鸠山走出浴室,将那一片暗红色锁在了门的另一头,然后擦好头发,从衣柜里挑了她最旧的一条长裙。
她再也不打算回这个地方了。
于是她将灶台的火开了起来,随便拿起一个锅子,装了水后置在灶台上,又跑到屋子另一端将门打开。
真纪背着一个不鼓也不瘪的黑色背包,里面是忍者的行当。她从窗户跳下去,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街区。她感觉到身后有不善的忍者气息,但当她跨入人多的地上时,那种气息就消失了。她顺着人流走,哪里人多就待在哪里。
几个小时过去,太阳已经快落山了,自己所在的那个巷子也被救火队的人封锁了。
她能闭上眼想象自己的公寓燃起来的样子——滚烟从窗户里冒出来,然后,橙红的火光就像这夕阳一般,舔舐着天边的残云,一片橙红融和一体。
她还能想象到,自己痛恨的那群人,想要以纵火的罪名将自己逮捕,但发现浴室里暗部的尸体后,怕暗杀平民的丑闻泄出,只得睁只眼闭只眼。自己大概还是会被找去审问,但即使证词漏洞百出,他们也没法把她怎样,因为她有把柄。
不,即使她没有做任何事,他们都可以把她抹杀——木叶高层想要抹杀掉一个普通下忍需要理由吗?
木叶并非灯火通宵的都城,到了一定的时间点街上总会寥落起来的,于是她站起身。
真纪一路保持警惕地走到了日向府邸前,认识宁次以来,她来过这里很多次,侍卫都认识她了,但这是她第一次叩响大门,并走了进去。
在她很小的时候,就发觉了自己的处境的不妙,她总能感觉到暗藏杀机的影子潜伏在她身后,一直跟着她一直跟着她,但当走到人多的地方或日向家附近时,那种感觉才会消失。在她进忍校的那一年,发生了一件事,让她肯定了,自己身后的眼睛正是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子的高管派来的。
也就是那一年,她开始在那间如今已被自己烧掉的公寓里独自生活。她今天本不想回去的,但有些事不得不做。
比如把身上洗干净,换上整洁但又破旧的衣服,练习一下表情。
她在一名侍卫的带领下敲了别院的门,然后一个眉目和宁次十分相似的女人接待了她。
用珠光宝气来形容那个女人是不恰当的,因为她戴的珠宝并不多,仅仅是耳上垂了两枚很内敛的黑曜石耳坠,身上着的和服是素雅的浅绿色。但她却是那么耀眼。就好像她的双眸,她的手腕,她的长发本身就会散发出珠宝的光辉,那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气质。
宁次的母亲,日向惠子夫人此时就站在自己面前。
真纪发觉自己的目光几乎要移不开了。她忙鞠躬,一番抱歉后,说道自己有很重要的事要与宁次讲,请夫人也在一旁听。她抬头,将发丝撩到耳后,用真诚的眼神望了一眼夫人的双眸,又恭敬的一鞠躬。
夫人莞尔一笑,将她领进了院子,然后,她看见了正坐在走道上观赏夕阳的宁次。
面对宁次惊讶的质问,真纪的目光忽如秋水一样柔软了下来,然后她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抬头时,她看见了宁次诧异的目光。
真纪过去的年岁里,或许从未露出过那样卑微的神情与姿态,但现在,他们三人坐在屋里,围着一张矮矮的方桌,真纪是客人,却比女仆还殷勤地倒茶,让宁次端着茶,看看她脸上的红晕,又看看被子里旋转的茶叶,不知道该不该喝。
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想说,小姑娘?”惠子说道,她感觉很不妥,但看着真纪耳边随着身体的起伏而摆动的碎发,并没有阻止。
“我……”她跪坐在褐色的垫子上,用一种怯怯的眼神望向夫人,又望向宁次,然后忽然往后退了一段距离,伸开手臂,指尖放到了垫子上,手指合拢不见一丝缝隙,身体压低,脖子是笔直的,但头几乎要碰到地上了,“请夫人收留我吧,拜托了。”
宁次震惊地睁大了眼睛——如果换了别人还没什么,但对方是鸠山真纪,她居然会行这样的鞠躬,简直卑微到了极点!这让他没听去在意她说了什么,随后他望向了她的母亲,他这才反应过来。
惠子倒是很平静,好像经常有人对她行这样的礼,哪怕对方是一个陌生的小女孩,她也不会觉得奇怪。
“只要一年,等我升上了中忍,我就离开,拜托了,”真纪抬头,眼睛里已经泛起了一点泪光,她的鼻尖红红的,“费用我会拼命做任务来还的,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。”
“你的家人呢?”惠子说道,她微皱起眉,声音柔和得像她和服上绣的花瓣,“你是没有地方住了吗?”
“我没有父母,只有奶奶,但我七岁的时候,她也离开了,”真纪低下头,看上去是一副强忍着眼泪的样子,“不知道夫人有没有听说,今天上午在樟树巷的那场火灾——烧起来的是我的住所,出门时门忘记关了,邻居借我的厨房用,然后就出事了。”
她擦了擦眼睛,“我在学校里只有宁次那么一个朋友的,所以……”
真纪没再往下说,而是抬头望着夫人的眼睛。她的余光瞥见宁次一脸见了鬼的表情。
宁次知道真纪无父无母,只有个奶奶,但不知道她老人家那么久前就过世了。他只知道进了忍校一段时间后,真纪整个人瘦了一圈,婴儿肥过早的消失在了她的脸颊上,同时消失的还有孩童特有的懵懂眼神——那种转变,就像见到父亲尸体后的自己。
她手紧握着玻璃杯,空气中的水汽在剔透的玻璃上冷凝,像蚯蚓一样从杯的上端扭动着划到下端,反射着晃眼的光点。她干燥的手指被浸湿了。
随后她又买了切成小小方形的抹茶糕,每碟里面只有四块;又买了三色丸子,里面包裹了雪菊屋特制的夹心,撒了细碎得几乎同粉末的果仁。村子里的甜品屋不少,雪菊屋的质量和价格都是数一数二的。她慢慢的品尝,一个丸子的滋味能让她回味很久,而更多的时间是在观察来来往往的路人和地面上的影子,当影子又开始拉长时,她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,这是她很多年来花钱花得最随心所欲的一次。
鸠山站起身往前走了几步,侧过头,若有若无的瞥了一眼甜品屋的屋顶。
她的住所在很偏的旧居民区,终年冷清清的,似乎住在那里的人都不愿出门,或是一出门就要走得远远的。她实在不愿意回去,但不得不回去一趟,于是她离开人群,拐过好几个弯,经过一棵特别高的樟树,走进了一条盘着山丘的斜巷。
她回到了自己的公寓,站在门口思忖了一会,把窗帘都拉上了,然后锁上门。光仍透过浅蓝色的窗帘布透了进来,只不过被削弱了好几层,苟延残喘地趴在边缘长了裂纹的餐桌上。她一边往浴室的方向走,一边随手将脱下来的衣服扔在地上。最后她像一条白鱼一样泡在浴缸里,水的冷意扒开燥热直浸到了她的骨子里。
也许是在外面灿烂的阳光里待太久了,浴室里的白炽灯格外昏暗。
屋子里只有滴答滴答的水声。
她闭着眼睛往后靠,先是双腿闭拢着抬出了水面,搭在浴缸的另一侧,再是抬起浸在水中的修长的手臂,水珠顺着肌肤滴下来撞击着水面,她弯曲的手指上赫然挂着一把水淋淋的苦无。她睁开眼。
带着狸猫面具,背着太刀的忍者站在自己面前。
意料之中的事。
她冷笑了一声,站起身,全身赤裸却毫无遮掩的站在了他面前。
他举起太刀,下一秒,殷红的血花溅落在了白色的瓷砖墙壁上,然后以不快不慢的速度滑下来,留下一道道长长的红痕,正像装着冰水的玻璃杯上冷凝的水珠流下来时的样子,只不过水珠是没有颜色的。
浴缸里的水被染红了,暗部忍者的尸块在里面一沉一浮。真纪将他脸上的面具揭下,看到他的表情定格在了惊恐的一瞬间。那是一张陌生的脸,于是她又把面具给他戴回去了。
就在刚刚,在她睁开眼的一瞬间,她的右眼发生了奇妙的变化,像是火一样的灼热,但是汇聚了一种说不明的力量,那种力量把她整个身体都充实起来了,让她心安。她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,好像根本什么都没做,就看见两道黑色的像刀刃一样的东西从自己面前划过,然后对方就变成了三截。
那个叫大蛇丸的人所说的话一股脑儿的涌了上来,她感到莫名兴奋——这不是咒印的力量,而大蛇丸说过让她注意自己的右眼,这也许就是他说过的独属于她自己的东西。
她站在浴缸旁边,用花洒冲走了地上和墙上的血迹,然后又仔细地清洗了自己的身体,闻着洗发水和沐浴露绵白的泡沫散发出的橄榄香——香味离得太近,盖住了那股血腥味。
鸠山走出浴室,将那一片暗红色锁在了门的另一头,然后擦好头发,从衣柜里挑了她最旧的一条长裙。
她再也不打算回这个地方了。
于是她将灶台的火开了起来,随便拿起一个锅子,装了水后置在灶台上,又跑到屋子另一端将门打开。
真纪背着一个不鼓也不瘪的黑色背包,里面是忍者的行当。她从窗户跳下去,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街区。她感觉到身后有不善的忍者气息,但当她跨入人多的地上时,那种气息就消失了。她顺着人流走,哪里人多就待在哪里。
几个小时过去,太阳已经快落山了,自己所在的那个巷子也被救火队的人封锁了。
她能闭上眼想象自己的公寓燃起来的样子——滚烟从窗户里冒出来,然后,橙红的火光就像这夕阳一般,舔舐着天边的残云,一片橙红融和一体。
她还能想象到,自己痛恨的那群人,想要以纵火的罪名将自己逮捕,但发现浴室里暗部的尸体后,怕暗杀平民的丑闻泄出,只得睁只眼闭只眼。自己大概还是会被找去审问,但即使证词漏洞百出,他们也没法把她怎样,因为她有把柄。
不,即使她没有做任何事,他们都可以把她抹杀——木叶高层想要抹杀掉一个普通下忍需要理由吗?
木叶并非灯火通宵的都城,到了一定的时间点街上总会寥落起来的,于是她站起身。
真纪一路保持警惕地走到了日向府邸前,认识宁次以来,她来过这里很多次,侍卫都认识她了,但这是她第一次叩响大门,并走了进去。
在她很小的时候,就发觉了自己的处境的不妙,她总能感觉到暗藏杀机的影子潜伏在她身后,一直跟着她一直跟着她,但当走到人多的地方或日向家附近时,那种感觉才会消失。在她进忍校的那一年,发生了一件事,让她肯定了,自己身后的眼睛正是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子的高管派来的。
也就是那一年,她开始在那间如今已被自己烧掉的公寓里独自生活。她今天本不想回去的,但有些事不得不做。
比如把身上洗干净,换上整洁但又破旧的衣服,练习一下表情。
她在一名侍卫的带领下敲了别院的门,然后一个眉目和宁次十分相似的女人接待了她。
用珠光宝气来形容那个女人是不恰当的,因为她戴的珠宝并不多,仅仅是耳上垂了两枚很内敛的黑曜石耳坠,身上着的和服是素雅的浅绿色。但她却是那么耀眼。就好像她的双眸,她的手腕,她的长发本身就会散发出珠宝的光辉,那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气质。
宁次的母亲,日向惠子夫人此时就站在自己面前。
真纪发觉自己的目光几乎要移不开了。她忙鞠躬,一番抱歉后,说道自己有很重要的事要与宁次讲,请夫人也在一旁听。她抬头,将发丝撩到耳后,用真诚的眼神望了一眼夫人的双眸,又恭敬的一鞠躬。
夫人莞尔一笑,将她领进了院子,然后,她看见了正坐在走道上观赏夕阳的宁次。
面对宁次惊讶的质问,真纪的目光忽如秋水一样柔软了下来,然后她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抬头时,她看见了宁次诧异的目光。
真纪过去的年岁里,或许从未露出过那样卑微的神情与姿态,但现在,他们三人坐在屋里,围着一张矮矮的方桌,真纪是客人,却比女仆还殷勤地倒茶,让宁次端着茶,看看她脸上的红晕,又看看被子里旋转的茶叶,不知道该不该喝。
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想说,小姑娘?”惠子说道,她感觉很不妥,但看着真纪耳边随着身体的起伏而摆动的碎发,并没有阻止。
“我……”她跪坐在褐色的垫子上,用一种怯怯的眼神望向夫人,又望向宁次,然后忽然往后退了一段距离,伸开手臂,指尖放到了垫子上,手指合拢不见一丝缝隙,身体压低,脖子是笔直的,但头几乎要碰到地上了,“请夫人收留我吧,拜托了。”
宁次震惊地睁大了眼睛——如果换了别人还没什么,但对方是鸠山真纪,她居然会行这样的鞠躬,简直卑微到了极点!这让他没听去在意她说了什么,随后他望向了她的母亲,他这才反应过来。
惠子倒是很平静,好像经常有人对她行这样的礼,哪怕对方是一个陌生的小女孩,她也不会觉得奇怪。
“只要一年,等我升上了中忍,我就离开,拜托了,”真纪抬头,眼睛里已经泛起了一点泪光,她的鼻尖红红的,“费用我会拼命做任务来还的,一定不会给您添麻烦。”
“你的家人呢?”惠子说道,她微皱起眉,声音柔和得像她和服上绣的花瓣,“你是没有地方住了吗?”
“我没有父母,只有奶奶,但我七岁的时候,她也离开了,”真纪低下头,看上去是一副强忍着眼泪的样子,“不知道夫人有没有听说,今天上午在樟树巷的那场火灾——烧起来的是我的住所,出门时门忘记关了,邻居借我的厨房用,然后就出事了。”
她擦了擦眼睛,“我在学校里只有宁次那么一个朋友的,所以……”
真纪没再往下说,而是抬头望着夫人的眼睛。她的余光瞥见宁次一脸见了鬼的表情。
宁次知道真纪无父无母,只有个奶奶,但不知道她老人家那么久前就过世了。他只知道进了忍校一段时间后,真纪整个人瘦了一圈,婴儿肥过早的消失在了她的脸颊上,同时消失的还有孩童特有的懵懂眼神——那种转变,就像见到父亲尸体后的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