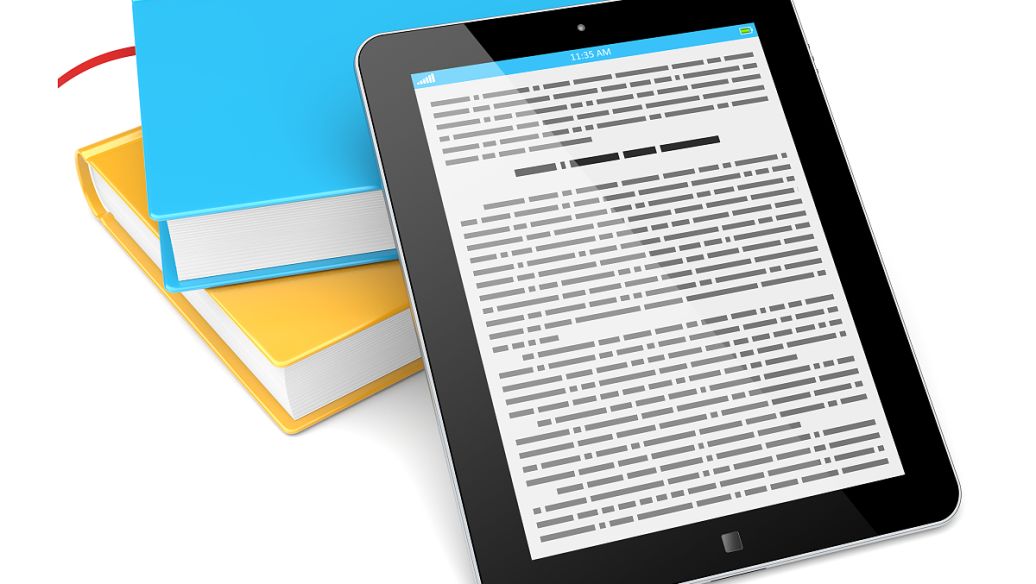宁次走出房间,轻轻合上了推门。真纪注视着他离开,门关上后,她的目光仍长长的停在褐色的门框上。她就那样一动不动的,三分钟后,她突然抽了抽肩膀,用手掩住了翘起的嘴角,被掐碎的笑声一点一点的,若有若无的压抑着的,从指缝里溢出来,像是一种抽噎,令人头皮发麻。她咬住了自己的食指关节,不让自己笑出来,但眼角的笑意却已经强烈成了扭曲变样的疯狂。
终于死了,那个老头,他终于死了。
她的眼神炽热起来,浓浓的杀意使得她周身开始发热。她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,但却无法向任何人倾诉,所有的一切,真正的真相与她的心意,只能她一个人承担,一个人消化。她感觉她像正在吃着角落里黑压压的影子,她将它像扯布匹一样扯下来,放入口中细细的嚼,滑腻腻的苦涩与辛辣顺着她的食道而下,然后永远消失。
终于死了,火影啊,你终于死了,就算我杀不了你,也会有其他人来帮我的。谢谢你了,大蛇丸。
她察觉到自己的双手正在出汗,而且在颤个不停,她将摆在床头上的一本不厚的小说掂在手里,发现颤得更厉害了。她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窗外的风呼啸而过,像瞬间闪烁的刀光,而那阵心跳声却扑通不停,紧张,急促,沉重,仿若鼓点。
她想起自己刚被日向家收养的那个晚上,她告诉宁次她之前说了谎话,却又编织了另一个谎言来盖过它。好吧,她是有那么一点点愧疚,但那个真相,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,没人会相信她,没人。
真纪的身体恢复得很快,没过多久就又活动自如了。她一改上个月的懒散,摘掉了身上所有的首饰,换了一套更合身的新忍服,发了狂的进行特训。
清水沐子上忍不是个善于管理学生的老师,但她教东西真的教得特别好,尤其是忍术。她擅长水,火两大遁术,隐匿气息,以及偷袭,真纪从她那学到了不少本领。值得一提的是她拥有极强自愈能力的血继限界,可惜这是无法传授的。
真纪每日大概五点与她在道场集合,特训的内容只有基本体术,火遁,以及咒印的控制,教授形式却是注重实际而富于变化的。下午,如果夫人有空的话,则是由她来教授幻术的破解,夫人很重视这项基本功,一直都没有教她施展幻术。等晚上与宁次在日向道场的体术对决训练完毕,她已经累得要散架了,但同时,一种满足感充实了她的每一个关节,这种快乐甚至高于懒散时期的那种快乐。
如果不能保证自己可以永远放心的松懈下去,就绝对不要停止保持警惕,那种偷出来的提心吊胆的“闲暇”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。
沐子不得不承认,尽管她并不希望与大蛇丸有瓜葛的人被分配到自己的班里,但真纪的确是她最看好的一个学生。明明是一个女孩子,一副瘦弱的样子,在战场上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,求知欲也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学生。
她翻看过真纪的在校档案,逃课次数已经达到上限了,但由于考试成绩优秀,教师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她笑了,这是典型的人后努力型学生,她没有偷懒,只是转移了学习场地罢了。
时间流逝得飞快,夜晚降临时已经倾下来几丝秋意了。而大蛇丸却一直没有出现。
“抱歉打扰贵府了。”披着黑色风衣,神色冷峻的高大男人和他身后的两个副手朝夫人鞠了一躬,“我们找鸠山真纪。”
真纪站在楼梯口,攥着拳头,而宁次站在她的身后,就在刚刚,他告诉她有情报部的人找她去录口供,具体是为了哪个案子他也并不清楚,于是她走出了房间,一步一步往前走,直到通往一楼的楼梯口前。
她的大脑飞快的运作着,把词词句句都翻腾了出来,组织成一条长长的链。该来的总会来的,她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他们来找自己,可能是她的住所失火,而浴室里有暗部尸体一案,也可能是自己与大蛇丸的瓜葛,也有可能就是多年前那起事件迟来的后续,但无论是因为哪一个,她明白,自己绝对是有去无回了。就算没有罪名,他们也会给她套上一个!
她深吸一口气,转头向宁次示意着,两人一起走下了楼梯。
她脚下一滑。
敢对别人狠,自然也敢对自己不客气。
川泽森太郎和他的两个副手没有进日向的宅邸,他们就伫立在门前,等候着鸠山真纪,但是他们最终只等到了她从楼梯上摔下来,摔得头破血流的消息。他咬了咬脸颊内侧,面对着日向夫人带着歉意的笑容,只能挥手作罢,毕竟上头给的时间还算宽裕,于是他做了让步,将期限推至了明天的上午九点,到了那个时候,不管她是昏迷着还是缺了条胳膊,都得跟着他去火影办公楼地下二层的审讯室走一趟。
鸠山摔得并不算太惨,忍者的恢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,到了深夜的时候,除了头上缠着一圈绷带让她觉得不大舒服,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,手脚的淤青根本不算什么。
夜色正浓,灰蓝色像织得极厚实的棉被,密不透风的挤占了每一寸天幕,将星光与明月都与大地隔绝了开来。在街上仍有几盏寥寥落落的灯,昏黄的灯光呈圆锥状,照过一只灰色或黑色的猫,或是几个双手插在口袋里小跑过的行人。
鸠山真纪坐在窗外那棵歪脖子树的枝干上,被掩于枝叶间。她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个位于十二号巷的药铺里,那是她从有记忆开始居住的地方,有个柜台,柜台后面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妇人,白发很多,妇人后面是又高又大几乎占据一面墙的药柜,由大概几十上百个抽屉组成,她认字便是从那些柜子字牌上开始的。“当归”、“决明子”,“莲子”,她对莲子印象特别深刻,那时候大概三岁。她闻着各种药味长大。那位老妇人是她的奶奶,不管到底是不是有真正血缘关系的,奶奶偶尔会从“甘草”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片状的东西给她吃,一股子怪味道,但她总是会在隔了很久后又要求来一个。药柜很旧,确切的来讲,她家里的一切都很旧,永远是干瘦的,有裂痕的,长着垢与霉斑的,阴沉的,琢磨不清的,神秘的。
她好像对一个人在家时的记忆特别深刻,好像那段记忆不断膨胀,扩大,将其它的记忆挤到了不易翻寻的边缘角落。它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,她一个人待在静悄悄的屋子里,扶着楼梯慢慢往下走,在屋子里越是安静的地方,她发出的动静也会跟着更小,仿佛有意要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她的目光掠过桌角,阳光恰好撒在那里,窄窄的几缕,使得她能清楚的看到桌子上的裂痕与褐色的痂,以及空气中一粒一粒的灰尘,明明它们在动,时间却像静止了一般。那时她站在最后一级木梯上,看着桌面山的光一动不动地,似乎是想和静止了的时间一起静止了。
她的房间在二楼,有个大书桌,兼有着书柜的功能,将她不大的房间挤占得满满的,书柜里面有成堆的卷轴和一沓一沓的书籍,从两头到正中央,从认字图书,神话怪谈到忍校课本,长篇悬疑小说到历史传记,血迹研究,忍术卷宗,大概有一百多本,那年六七岁的样子。搬到樟树巷后,她只带走了三十来本,一直反复读到了今年,直至它们被大火烧光。里面的内容她几乎是倒背如流了。
从口袋里掏出烟盒,将一支烟抖了出来,她的指头轻轻捏着海绵烟头,忽的停下了动作,半晌,她还是将烟塞了回去,放入口袋中。
她爬窗回到了房间里,扫了一眼,就像当初在樟树巷公寓里时一样。她只抓了一把钱币和一条非常漂亮的玉坠塞入裤子口袋中。她的目光又在那套红黑相间的浴衣上停留了一会,很可惜,再过两天就有祭典了,那时她就可以穿上这套贵气漂亮的浴衣,画个淡妆,和宁次去南贺川散步……
她出门,穿过走廊来到宁次的房门前,轻轻敲了敲,“宁次,你睡了吗?”
“真纪?你有事吗?”声音隔着门传过来,紧接着是赤脚踩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。
“没什么,晚安!”
宁次唰地推开房门,但走廊上静悄悄的,不见人影,只有微弱的烛光,像瞌睡人的眼。
他疑惑的挑起眉毛,但还是关上门,轻轻踱步回了桌前。桌面上摆着白纸和黑笔,纸面上的字写了又划,仅有的没有被划掉的词是“礼物备选”,“书”以及其一旁用括号围起来的小字“关于火遁忍术”。
终于死了,那个老头,他终于死了。
她的眼神炽热起来,浓浓的杀意使得她周身开始发热。她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,但却无法向任何人倾诉,所有的一切,真正的真相与她的心意,只能她一个人承担,一个人消化。她感觉她像正在吃着角落里黑压压的影子,她将它像扯布匹一样扯下来,放入口中细细的嚼,滑腻腻的苦涩与辛辣顺着她的食道而下,然后永远消失。
终于死了,火影啊,你终于死了,就算我杀不了你,也会有其他人来帮我的。谢谢你了,大蛇丸。
她察觉到自己的双手正在出汗,而且在颤个不停,她将摆在床头上的一本不厚的小说掂在手里,发现颤得更厉害了。她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窗外的风呼啸而过,像瞬间闪烁的刀光,而那阵心跳声却扑通不停,紧张,急促,沉重,仿若鼓点。
她想起自己刚被日向家收养的那个晚上,她告诉宁次她之前说了谎话,却又编织了另一个谎言来盖过它。好吧,她是有那么一点点愧疚,但那个真相,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,没人会相信她,没人。
真纪的身体恢复得很快,没过多久就又活动自如了。她一改上个月的懒散,摘掉了身上所有的首饰,换了一套更合身的新忍服,发了狂的进行特训。
清水沐子上忍不是个善于管理学生的老师,但她教东西真的教得特别好,尤其是忍术。她擅长水,火两大遁术,隐匿气息,以及偷袭,真纪从她那学到了不少本领。值得一提的是她拥有极强自愈能力的血继限界,可惜这是无法传授的。
真纪每日大概五点与她在道场集合,特训的内容只有基本体术,火遁,以及咒印的控制,教授形式却是注重实际而富于变化的。下午,如果夫人有空的话,则是由她来教授幻术的破解,夫人很重视这项基本功,一直都没有教她施展幻术。等晚上与宁次在日向道场的体术对决训练完毕,她已经累得要散架了,但同时,一种满足感充实了她的每一个关节,这种快乐甚至高于懒散时期的那种快乐。
如果不能保证自己可以永远放心的松懈下去,就绝对不要停止保持警惕,那种偷出来的提心吊胆的“闲暇”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。
沐子不得不承认,尽管她并不希望与大蛇丸有瓜葛的人被分配到自己的班里,但真纪的确是她最看好的一个学生。明明是一个女孩子,一副瘦弱的样子,在战场上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,求知欲也明显高于其他几个学生。
她翻看过真纪的在校档案,逃课次数已经达到上限了,但由于考试成绩优秀,教师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她笑了,这是典型的人后努力型学生,她没有偷懒,只是转移了学习场地罢了。
时间流逝得飞快,夜晚降临时已经倾下来几丝秋意了。而大蛇丸却一直没有出现。
“抱歉打扰贵府了。”披着黑色风衣,神色冷峻的高大男人和他身后的两个副手朝夫人鞠了一躬,“我们找鸠山真纪。”
真纪站在楼梯口,攥着拳头,而宁次站在她的身后,就在刚刚,他告诉她有情报部的人找她去录口供,具体是为了哪个案子他也并不清楚,于是她走出了房间,一步一步往前走,直到通往一楼的楼梯口前。
她的大脑飞快的运作着,把词词句句都翻腾了出来,组织成一条长长的链。该来的总会来的,她已经做好了准备。他们来找自己,可能是她的住所失火,而浴室里有暗部尸体一案,也可能是自己与大蛇丸的瓜葛,也有可能就是多年前那起事件迟来的后续,但无论是因为哪一个,她明白,自己绝对是有去无回了。就算没有罪名,他们也会给她套上一个!
她深吸一口气,转头向宁次示意着,两人一起走下了楼梯。
她脚下一滑。
敢对别人狠,自然也敢对自己不客气。
川泽森太郎和他的两个副手没有进日向的宅邸,他们就伫立在门前,等候着鸠山真纪,但是他们最终只等到了她从楼梯上摔下来,摔得头破血流的消息。他咬了咬脸颊内侧,面对着日向夫人带着歉意的笑容,只能挥手作罢,毕竟上头给的时间还算宽裕,于是他做了让步,将期限推至了明天的上午九点,到了那个时候,不管她是昏迷着还是缺了条胳膊,都得跟着他去火影办公楼地下二层的审讯室走一趟。
鸠山摔得并不算太惨,忍者的恢复力也是不容小觑的,到了深夜的时候,除了头上缠着一圈绷带让她觉得不大舒服,其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,手脚的淤青根本不算什么。
夜色正浓,灰蓝色像织得极厚实的棉被,密不透风的挤占了每一寸天幕,将星光与明月都与大地隔绝了开来。在街上仍有几盏寥寥落落的灯,昏黄的灯光呈圆锥状,照过一只灰色或黑色的猫,或是几个双手插在口袋里小跑过的行人。
鸠山真纪坐在窗外那棵歪脖子树的枝干上,被掩于枝叶间。她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时代那个位于十二号巷的药铺里,那是她从有记忆开始居住的地方,有个柜台,柜台后面是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妇人,白发很多,妇人后面是又高又大几乎占据一面墙的药柜,由大概几十上百个抽屉组成,她认字便是从那些柜子字牌上开始的。“当归”、“决明子”,“莲子”,她对莲子印象特别深刻,那时候大概三岁。她闻着各种药味长大。那位老妇人是她的奶奶,不管到底是不是有真正血缘关系的,奶奶偶尔会从“甘草”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片状的东西给她吃,一股子怪味道,但她总是会在隔了很久后又要求来一个。药柜很旧,确切的来讲,她家里的一切都很旧,永远是干瘦的,有裂痕的,长着垢与霉斑的,阴沉的,琢磨不清的,神秘的。
她好像对一个人在家时的记忆特别深刻,好像那段记忆不断膨胀,扩大,将其它的记忆挤到了不易翻寻的边缘角落。它那么清晰又那么遥远,她一个人待在静悄悄的屋子里,扶着楼梯慢慢往下走,在屋子里越是安静的地方,她发出的动静也会跟着更小,仿佛有意要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她的目光掠过桌角,阳光恰好撒在那里,窄窄的几缕,使得她能清楚的看到桌子上的裂痕与褐色的痂,以及空气中一粒一粒的灰尘,明明它们在动,时间却像静止了一般。那时她站在最后一级木梯上,看着桌面山的光一动不动地,似乎是想和静止了的时间一起静止了。
她的房间在二楼,有个大书桌,兼有着书柜的功能,将她不大的房间挤占得满满的,书柜里面有成堆的卷轴和一沓一沓的书籍,从两头到正中央,从认字图书,神话怪谈到忍校课本,长篇悬疑小说到历史传记,血迹研究,忍术卷宗,大概有一百多本,那年六七岁的样子。搬到樟树巷后,她只带走了三十来本,一直反复读到了今年,直至它们被大火烧光。里面的内容她几乎是倒背如流了。
从口袋里掏出烟盒,将一支烟抖了出来,她的指头轻轻捏着海绵烟头,忽的停下了动作,半晌,她还是将烟塞了回去,放入口袋中。
她爬窗回到了房间里,扫了一眼,就像当初在樟树巷公寓里时一样。她只抓了一把钱币和一条非常漂亮的玉坠塞入裤子口袋中。她的目光又在那套红黑相间的浴衣上停留了一会,很可惜,再过两天就有祭典了,那时她就可以穿上这套贵气漂亮的浴衣,画个淡妆,和宁次去南贺川散步……
她出门,穿过走廊来到宁次的房门前,轻轻敲了敲,“宁次,你睡了吗?”
“真纪?你有事吗?”声音隔着门传过来,紧接着是赤脚踩在木质地板上的声音。
“没什么,晚安!”
宁次唰地推开房门,但走廊上静悄悄的,不见人影,只有微弱的烛光,像瞌睡人的眼。
他疑惑的挑起眉毛,但还是关上门,轻轻踱步回了桌前。桌面上摆着白纸和黑笔,纸面上的字写了又划,仅有的没有被划掉的词是“礼物备选”,“书”以及其一旁用括号围起来的小字“关于火遁忍术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