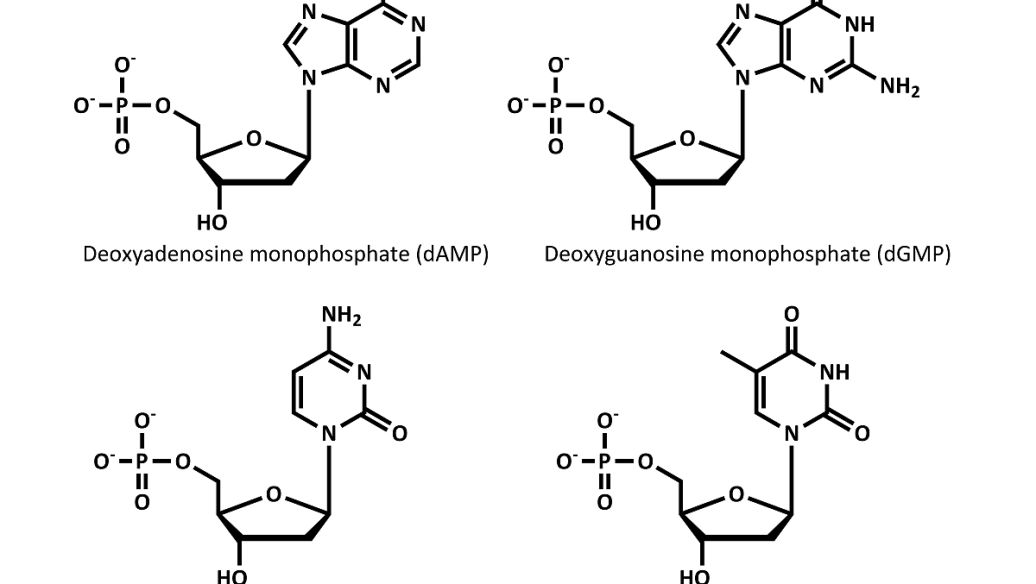皇城里有一株梅。
这株梅,活了几百年,然而它久久不开花,不结果,久到无人问津,被遗弃在一座破旧的宫殿里,年复一年的守着一片孤寂与清冷,漫天的霜雪里,它光秃秃的枝干盛着残雪,竟无花可开,也无叶可依。
也无人发觉它立在这里,孤零零的,像这皇宫里零星半点的暖意,难以叫人察觉。但它欢喜这清净,长久的岁月,它的枝干高过院墙,偶尔能看到殿外路过的宫女,更远的地方,人就多了,也热闹了,就更冷了。——始终不曾有人为它驻足停留,它因而不在乎开花与否,花既无人看,也不必开。
直到那扇殿门被一双冻得通红的手推开,进来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,那时啊这梅就立在院地里,看一场纷飞的白雪,从开始下到结束,它用枝桠盛的满满的。门开,惊得它心头一颤,雪簌簌地从枝头落下,它回头,正对上少年双眸,忽地愣住了,想笑,那样好看的眉眼,不是初见呢。
见过的吧,它想,可是忆不起何时何地,许是在梦里,是不经意的惊鸿一瞥,清冷澄明,如雪上初晴,熠熠生辉。
少年的身后,是为他送用具的老奴,独自替他拾掇着破败的宫殿。那老奴怜他无端受困,为他图个念想,特地向他讲了这梅的故事,他说相传有位巫族老人,说这梅是守护的意思,当它开花的时候,王朝会迎来一个盛世。然而上一个朝代没能等到,这株梅不开花,大家都不信了,可这梅年年长绿叶呢,活的这样久,兴许真有点灵性。
那少年不说话,兀自沉默着,落入这样的境地,脸上却是平静,就在树底下立着。梅很想告诉他,那老奴只说对了一半,是有那么一位老人,说它是魂族,是守护的意思,却没说花开就是盛世。可梅没法叫少年信或不信,它还不能凝聚成人形,也不能说话,故友重逢,梅很欢喜,却也不能送少年一份见面礼。
——那要不要先打个招呼呢?梅小心翼翼地晃晃枝干,却在无声的惊呼中落下一摊雪。
雪渗进脖颈凉的很,梅立刻不敢动了,那少年也不恼,他望着梅许久,似乎在想些什么,终究抚着苍虬层叠的树干喃喃问道:“你是白梅,还是红梅呢?”
梅忽地就给他问住了,它不知道呢,它没开过花,不知道呢。
长久的沉默,那少年还只是笑,“花开就知道了。”
算是互相打过招呼,少年自此便在这座冷宫住下了。冷宫冷宫,不但冷清,也透风,那窗户是无论如何也关不上的,只是少年并不在意。有月色的时候,他索性就坐在窗边,借一地白雪看书,梅在院子里,低低枝桠,也能瞧见少年捧书的模样,想要凑近些,却不能,它的枝桠到底不够长。
直至冰雪消融,迎来了春天,梅开始长新叶,青翠的,初夏就十分茂密了。那少年时常在树下练剑,梅觉得好,便也挥动枝叶给他鼓舞,落下一地窸窣。少年在落叶中潇洒舞剑的身影,梅是喜欢的,然而这少年十分不解风情,拾起叶子笑它:“秋天还没到就这样落叶,怕是要秃顶。”
有时候少年也会待在树下看书,薄薄的纸张一页翻过一页,梅拢好叶子,替他腾出一个荫地,又落一片叶在他肩上,陪着他看。偶尔恶作剧般,漏下一缕阳光,照在书面上亮的晃眼,少年也不躲,仍旧安安静静的看着。
“你认字吗?”少年忽然问,梅摇摇头,像随风轻盈而悠长的歌。
“我教你吧,”少年笑笑,豆大的字一顿一顿的被念出来,像是在数数。
“绸缪束薪,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,见此良人?子兮子兮,如此良人何?”
“子兮,你的名字就叫子兮如何?”
少年用纸用笔,把两个字单独写出来给它看。
“子兮,念着很好听呢。”
梅也在心里默念着,子兮,嘴角不自觉就上扬。
果然很好听。
守着空旷的宫殿一日复一日,便常常缺少时间的概念,卧病在床的皇帝厌倦了皇子们的争斗,终于记起他那丢弃在冷宫里的儿子,把他迎了出去。少年离开宫殿的那一天,梅在唱歌,它的绿叶在风中轻摇,低声似风鸣,“今夕何夕,见此良人,子兮子兮,如此良人何?”
宫殿又不可避免的安静了下来。
宫殿从前也安静,少年看书的时候,就连梅也收拢树枝不愿打扰,少年不说话,梅也陪着他,只是那时,有个人在身旁,看着不说话也觉得慰藉。梅让自己的叶子随风飘向皇城各地,想从宫女们的口中探求少年的消息,它不想少年重新回到这里,辛苦的陪它一起孤寂,却又渴望再看到他,即便只是路过这里。
它想,要是自己能凝聚成人形就好了。从前他也问那位老人,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凝聚成人形呢?”
“当你想的时候。”
“我现在就想啊。”
“当你很想很想的时候。”
梅终于在自己叶子即将散尽的时候得知了少年继位的消息,那时它已秃顶好几回了,少年也不再是少年,远远望见,已经是一个男人的高大模样。梅想,它应当送故人一份大礼,既然那位老奴说花开就是盛世,那它就送他一场花开吧。
在纷飞的雪中,它得见男人的登基大典,那一天,它开了一树的红梅,在阳光的照耀下鲜红的刺眼。他坐在树枝上,层层花瓣掩去身形,远处尽是嘈杂,男人盛装走上阶梯,忽然朝他一瞥,雪中那样清冷而平静的一眼,梅恍惚着记起了自己的梦。
所以说是见过的,梅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好极了,他笑,笑的花枝乱颤,差点从树枝上摔下去。
他忽然就觉得很满足。
这株梅,活了几百年,然而它久久不开花,不结果,久到无人问津,被遗弃在一座破旧的宫殿里,年复一年的守着一片孤寂与清冷,漫天的霜雪里,它光秃秃的枝干盛着残雪,竟无花可开,也无叶可依。
也无人发觉它立在这里,孤零零的,像这皇宫里零星半点的暖意,难以叫人察觉。但它欢喜这清净,长久的岁月,它的枝干高过院墙,偶尔能看到殿外路过的宫女,更远的地方,人就多了,也热闹了,就更冷了。——始终不曾有人为它驻足停留,它因而不在乎开花与否,花既无人看,也不必开。
直到那扇殿门被一双冻得通红的手推开,进来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,那时啊这梅就立在院地里,看一场纷飞的白雪,从开始下到结束,它用枝桠盛的满满的。门开,惊得它心头一颤,雪簌簌地从枝头落下,它回头,正对上少年双眸,忽地愣住了,想笑,那样好看的眉眼,不是初见呢。
见过的吧,它想,可是忆不起何时何地,许是在梦里,是不经意的惊鸿一瞥,清冷澄明,如雪上初晴,熠熠生辉。
少年的身后,是为他送用具的老奴,独自替他拾掇着破败的宫殿。那老奴怜他无端受困,为他图个念想,特地向他讲了这梅的故事,他说相传有位巫族老人,说这梅是守护的意思,当它开花的时候,王朝会迎来一个盛世。然而上一个朝代没能等到,这株梅不开花,大家都不信了,可这梅年年长绿叶呢,活的这样久,兴许真有点灵性。
那少年不说话,兀自沉默着,落入这样的境地,脸上却是平静,就在树底下立着。梅很想告诉他,那老奴只说对了一半,是有那么一位老人,说它是魂族,是守护的意思,却没说花开就是盛世。可梅没法叫少年信或不信,它还不能凝聚成人形,也不能说话,故友重逢,梅很欢喜,却也不能送少年一份见面礼。
——那要不要先打个招呼呢?梅小心翼翼地晃晃枝干,却在无声的惊呼中落下一摊雪。
雪渗进脖颈凉的很,梅立刻不敢动了,那少年也不恼,他望着梅许久,似乎在想些什么,终究抚着苍虬层叠的树干喃喃问道:“你是白梅,还是红梅呢?”
梅忽地就给他问住了,它不知道呢,它没开过花,不知道呢。
长久的沉默,那少年还只是笑,“花开就知道了。”
算是互相打过招呼,少年自此便在这座冷宫住下了。冷宫冷宫,不但冷清,也透风,那窗户是无论如何也关不上的,只是少年并不在意。有月色的时候,他索性就坐在窗边,借一地白雪看书,梅在院子里,低低枝桠,也能瞧见少年捧书的模样,想要凑近些,却不能,它的枝桠到底不够长。
直至冰雪消融,迎来了春天,梅开始长新叶,青翠的,初夏就十分茂密了。那少年时常在树下练剑,梅觉得好,便也挥动枝叶给他鼓舞,落下一地窸窣。少年在落叶中潇洒舞剑的身影,梅是喜欢的,然而这少年十分不解风情,拾起叶子笑它:“秋天还没到就这样落叶,怕是要秃顶。”
有时候少年也会待在树下看书,薄薄的纸张一页翻过一页,梅拢好叶子,替他腾出一个荫地,又落一片叶在他肩上,陪着他看。偶尔恶作剧般,漏下一缕阳光,照在书面上亮的晃眼,少年也不躲,仍旧安安静静的看着。
“你认字吗?”少年忽然问,梅摇摇头,像随风轻盈而悠长的歌。
“我教你吧,”少年笑笑,豆大的字一顿一顿的被念出来,像是在数数。
“绸缪束薪,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,见此良人?子兮子兮,如此良人何?”
“子兮,你的名字就叫子兮如何?”
少年用纸用笔,把两个字单独写出来给它看。
“子兮,念着很好听呢。”
梅也在心里默念着,子兮,嘴角不自觉就上扬。
果然很好听。
守着空旷的宫殿一日复一日,便常常缺少时间的概念,卧病在床的皇帝厌倦了皇子们的争斗,终于记起他那丢弃在冷宫里的儿子,把他迎了出去。少年离开宫殿的那一天,梅在唱歌,它的绿叶在风中轻摇,低声似风鸣,“今夕何夕,见此良人,子兮子兮,如此良人何?”
宫殿又不可避免的安静了下来。
宫殿从前也安静,少年看书的时候,就连梅也收拢树枝不愿打扰,少年不说话,梅也陪着他,只是那时,有个人在身旁,看着不说话也觉得慰藉。梅让自己的叶子随风飘向皇城各地,想从宫女们的口中探求少年的消息,它不想少年重新回到这里,辛苦的陪它一起孤寂,却又渴望再看到他,即便只是路过这里。
它想,要是自己能凝聚成人形就好了。从前他也问那位老人,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凝聚成人形呢?”
“当你想的时候。”
“我现在就想啊。”
“当你很想很想的时候。”
梅终于在自己叶子即将散尽的时候得知了少年继位的消息,那时它已秃顶好几回了,少年也不再是少年,远远望见,已经是一个男人的高大模样。梅想,它应当送故人一份大礼,既然那位老奴说花开就是盛世,那它就送他一场花开吧。
在纷飞的雪中,它得见男人的登基大典,那一天,它开了一树的红梅,在阳光的照耀下鲜红的刺眼。他坐在树枝上,层层花瓣掩去身形,远处尽是嘈杂,男人盛装走上阶梯,忽然朝他一瞥,雪中那样清冷而平静的一眼,梅恍惚着记起了自己的梦。
所以说是见过的,梅觉得自己的记忆力好极了,他笑,笑的花枝乱颤,差点从树枝上摔下去。
他忽然就觉得很满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