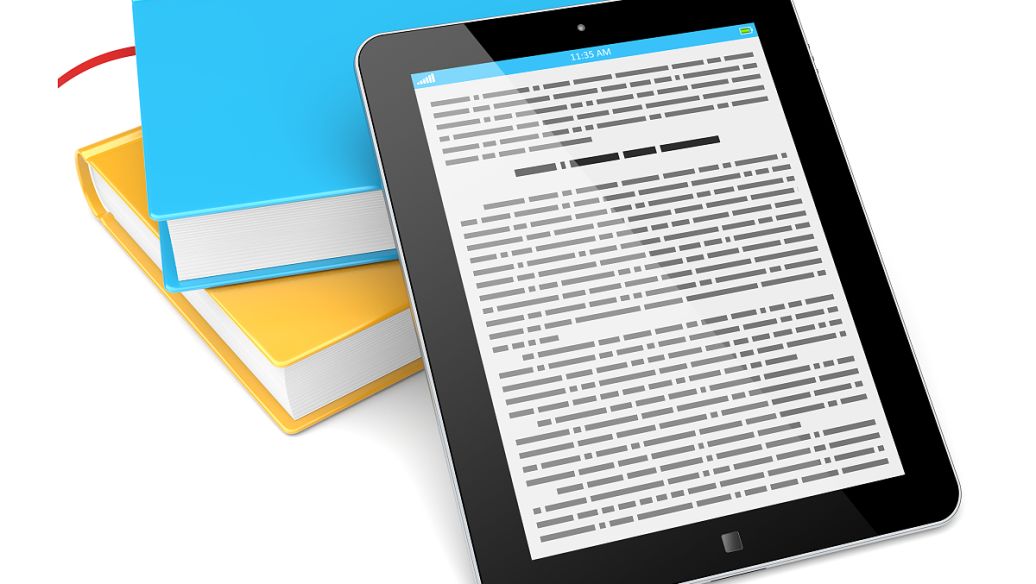《紅樓夢》第六十七回之商榷 王以安 撰
現存《紅樓夢》第六十七回有兩種板本,《程乙本》序言說「是書沿傳既久,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祕稿,繁簡歧出,前後錯見。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,題同文異,燕石莫辨。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為定本。」存世諸本中唯「戚序」、「列藏」及「甲辰」三者近似而迥異「程高」、「蒙府」等「普及本」,細審均非作者原本未能定於一尊。
茲以「假語村言」採用《影梅庵憶語》文字略為探勘六十七回兩種板本,其以「普及本」為基準,初步取得驗證如下:
《庵憶》云:「家君見之,訝且歎,」書載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:我的兒,你聽見了沒有?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,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麽,不知爲什麽自刎了。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裏去了。真正奇怪的事,叫人意想不到。寶釵聽了,並不在意。便說道:俗語說的好,天有不測風雲,人有旦夕禍福。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。「薛姨媽」為薛家「家君」,「你聽見了沒有」為「見之」。「真正奇怪的事」是「訝」,「叫人意想不到」是「歎」。本處有《靖藏眉批》「寶卿不以為怪,雖慰此言,以其母不然,亦知何為□□□□寶卿心機,余已此又是□□」以「怪」寫「訝」,注記妥當。
《庵憶》云:「余嘗過三吳、白下,遍收筐箱中,蓋面大塊,」書載薛蟠打江南回來是寫「余嘗過三吳、白下,」,帶有虎丘土物是三吳地界。一箱是綢緞綾錦洋貨,一箱卻是些筆、墨、紙、硯、各色箋紙、香袋、香珠、扇子、扇墜、花粉、胭脂等物,是寫「遍收筐箱中」。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,與薛蟠毫無差錯,則寫「蓋面大塊」。
《庵憶》云:「群美之,群妒之,同上虎邱。與予指點舊遊,重理前事,吳門知姬者,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。」書載薛蟠給寶釵一箱筆、墨、紙、硯、各色箋紙、香袋、香珠、扇子、扇墜、花粉、胭脂等物。外有「虎丘」帶來的自行人、酒令兒,水銀灌的打筋斗小小子,沙子燈,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,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。又有在「虎丘」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,與薛蟠毫無差錯。兩言虎丘巧是「同上虎邱」?寶釵將那些玩意兒一分一分配合妥當,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,賞賜來使,說見面再謝。是寫「群美之」。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,反自觸物傷情,想起父母雙亡,又無兄弟,寄居親戚家中,那裏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?想到這裏,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。這反是特寫「妒之」了。寶玉挨著黛玉坐下,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著細瞧,故意問這是什麼,叫什麼名字。那是什麼做的,這樣齊整。這是什麼,要他做什麼使用。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。像煞「與予指點舊遊」。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,是隱喻「重理前事」句。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,解了悲痛,可謂「吳門知姬者」。黛玉道:自家姊妹,這倒不必。只是到他那邊,薛大哥回來了,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迹兒,我去聽聽,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,則解作「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」。「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迹兒,」是「咸稱其俊識」。「只當回了家鄉一趟」是「得所歸」,把回鄉作歸鄉。
《庵憶》云:「謂姬何暇精細及此。」書載薛家夥計內中一個道:別是這麽著罷?衆人問怎麽樣,那人道: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,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。他原會些武藝,又有力量,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,特意跟他去,在背地擺佈他,也未可知。「那樣個伶俐人」寫「何暇精細」。「未必是真」寫「及此」。本處有《靖藏眉批》「似糊塗卻不糊塗,若非有風緣根基有之人,豈能有此□□□姣姣冊之副者也。」其中「不糊塗」為「精細」也。
《庵憶》云:「復遍覓之,」書載衆人問薛蟠: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?薛蟠說:城裏城外,那裏沒有找到?不怕你們笑話,我找不著他,還哭了一場呢。言畢,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,不像往日高興。「城裏城外,那裏沒有找到?」是「復遍覓之」,本處有《靖藏眉批》「獃兄也是有情之人。」作為標記顯然。
由以上五處作成比較,發覺有「普及本」中「黛玉道:自家姊妹,這倒不必。只是到他那邊,薛大哥回來了,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迹兒,我去聽聽,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」一段文字與「戚序本」之記載「黛玉原不願意爲送這些東西來就特特的道謝去,不過一時見了,說一聲就完了。今被寶玉說得有理,難以推託,無可奈何只得同寶玉去了」異趣。後者頗不見容於《影梅庵憶語》「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」的解讀,知是以「普及本」為勝出。
意外運用《孟子、齊人章》假語村言解讀之下卻又另有發現。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,其良人出,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,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:良人出,則必饜酒肉而後反;問其與飲食者,盡富貴也,而未嘗有顯者來,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。蚤起,施從良人之所之,遍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閒,之祭者,乞其餘;不足,又顧而之他,此其為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告其妾曰:良人者,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。與其妾訕其良人,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,施施從外來,驕其妻妾。」這是眾所周知的故事。
作者套寫長篇大論是要分段來表達,掩人耳目。話說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」,書中是以賈璉作齊人,剛好他有鳳姐、平兒的一妻一妾。三十九回有《批注》說「妙文!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,此則先見鳳姐後見平兒也。何錯綜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?」呼應第六回中「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。」《批注》說「記清。」那才是姥姥見平兒之處,批書人特在點醒「處室」,也就是房室的區處之意。
二十一回載「那個賈璉,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,獨寢了兩夜,便十分難熬,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。」是寫「其良人出,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」。然後二十二回鳳姐問賈璉以寶釵生日怎麼作?是寫「其妻問所與飲食者」也。賈璉答話「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,這會子倒沒了主意?」含有玄機,此處是寫「則盡富貴也」,多大生日實寫「富貴」二字。
劉姥姥遊大觀園時,鳳姐與鴛鴦商議要拿他取個笑兒,是寫「其妻告其妾曰」。鴛鴦笑道: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篾片相公,拿他取笑兒,是以「外頭老爺們」寫「良人出」。姥姥逗笑,史湘雲噴飯,薛姨媽噴茶,失控場面是寫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」,把吃下去的東西都反出來了。劉姥姥誇鵪鶉蛋小巧,鳳姐兒說是一兩銀子一個,寫「問其與飲食者,盡富貴也」,富貴人家才吃得起。劉姥姥好不容易撮起一個蛋要吃,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,是寫「而未嘗」。劉姥姥歎息怪道說禮出大家,是寫「有顯者來」,大家是顯貴之家。姥姥失蹤,眾人尋找不見,襲人說我且瞧瞧去,是寫「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」。
四十六回載寶玉藏身山子石後,鴛鴦、襲人、襲人三人「唬了一跳」,是寫「蚤起」,跳蚤也。「看你低著頭過去了,進了院子就出來了,逢人就問。我在那裏好笑,只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,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,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。」是寫「施從良人之所之,遍國中無與立談者。」逢人就問,是「遍國中」,藏藏躲躲則是「無與立談者」,此處是把良人當成姨娘了。
賈敬死後停靈城外鐵檻寺裏,是寫「卒之東郭墦閒」,鐵檻寺本名饅頭庵,比擬土饅頭自有其道理在。賈璉因賈敬停靈在家,垂涎二尤,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,是「之祭者乞其餘」,賈珍是喪祭者。俞祿回說給銀仍欠六百零十兩,是寫「不足」。賈珍打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主意,賈蓉問過尤氏,說剩的三百兩交與老娘收了。這是寫「又顧而之他」,「顧」是尤氏,「之」是老娘。賈璉表態挪借銀兩,借機親近二姐以饜其欲,大開尊口是「此其為饜足之道也」,說得頭頭是道。解讀到此,接下去問題可就來了。鳳姐問完興兒話後,相對於「普及本」的簡略敘述「這裏鳳姐才和平兒說:你都聽見了?這才好呢。平兒也不敢答言,只好陪笑兒」不足以解讀「其妻歸告其妾曰:良人者,所仰望而終身也,今若此。與其妾訕其良人」而「戚序本」卻有下面這段文字供作解讀。
「且說鳳姐見興兒出去,回頭向平兒說:方纔興兒說的話,你都聽見了沒有?平兒說:我都聽見了。鳳姐說:天下那有這樣沒臉的男人!吃著碗裏,看著鍋裏。見一個,愛一個。真成了喂不飽的狗,實在的是個棄舊迎新壞貨。只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!他別想著俗語說的家花那有野花香的話,他要信了這個話,可就大錯了。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狠沒臉,親戚朋友見不得的事出來,他纔罷手呢!平兒在一旁勸道:奶奶生氣卻是該的。但奶奶的身子纔好了,也不可過於氣惱。看二爺自從鮑二的女人那一件事之後,到狠收了心,好了呢。如今爲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?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。」鳳姐回頭向平兒說話是「其妻歸告其妾曰」。「天下那有這樣沒臉的男人」寫「良人者」。「吃著碗裏,看著鍋裏」寫「所仰望」,鍋比碗要大。「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狠沒臉,親戚朋友見不得的事出來,他纔罷手」寫「而終身也」,早晚是時間,罷手是終了。平兒說「如今爲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?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」,寫「今若此」。鳳姐背地大罵賈璉是「與其妾訕其良人」,反觀「普及本」卻始終沒有責罵的話語。
接著第六十八回載二姐行禮,鳳姐下座還禮,口說願作妹子,容一席之地安身,死也願意。說著,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尤二姐見了這般,也不免滴下淚來,二人對見了禮,分序座下。是即「而相泣於中庭」,「庭」字通作「廷」解。等賈璉事畢回來,先到了新房中,已竟悄悄的封鎖,老頭子細說原委,賈璉只在鐙中跌足。是寫「而良人未之知也」。賈璉見了賈母和家中人,回來見鳳姐,未免臉上有些愧色。是「施施從外來」。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顔,同尤二姐一同出迎,敘了寒溫。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,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,驕矜之容。是寫「驕其妻妾」。
作者大費周章把《齊人篇》從頭到尾套寫完全,刻劃出身側福晉的「繼后那拉氏」一妻一妾公案,卻又意外地作為驗證六十七回的工具。而總上所得結果,不難窺知兩種版本各有優勝,不能有所取捨。唯有透過不斷的解讀判別,才能還《紅樓夢》以本來面目。
現存《紅樓夢》第六十七回有兩種板本,《程乙本》序言說「是書沿傳既久,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祕稿,繁簡歧出,前後錯見。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,題同文異,燕石莫辨。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為定本。」存世諸本中唯「戚序」、「列藏」及「甲辰」三者近似而迥異「程高」、「蒙府」等「普及本」,細審均非作者原本未能定於一尊。
茲以「假語村言」採用《影梅庵憶語》文字略為探勘六十七回兩種板本,其以「普及本」為基準,初步取得驗證如下:
《庵憶》云:「家君見之,訝且歎,」書載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:我的兒,你聽見了沒有?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,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麽,不知爲什麽自刎了。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裏去了。真正奇怪的事,叫人意想不到。寶釵聽了,並不在意。便說道:俗語說的好,天有不測風雲,人有旦夕禍福。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。「薛姨媽」為薛家「家君」,「你聽見了沒有」為「見之」。「真正奇怪的事」是「訝」,「叫人意想不到」是「歎」。本處有《靖藏眉批》「寶卿不以為怪,雖慰此言,以其母不然,亦知何為□□□□寶卿心機,余已此又是□□」以「怪」寫「訝」,注記妥當。
《庵憶》云:「余嘗過三吳、白下,遍收筐箱中,蓋面大塊,」書載薛蟠打江南回來是寫「余嘗過三吳、白下,」,帶有虎丘土物是三吳地界。一箱是綢緞綾錦洋貨,一箱卻是些筆、墨、紙、硯、各色箋紙、香袋、香珠、扇子、扇墜、花粉、胭脂等物,是寫「遍收筐箱中」。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,與薛蟠毫無差錯,則寫「蓋面大塊」。
《庵憶》云:「群美之,群妒之,同上虎邱。與予指點舊遊,重理前事,吳門知姬者,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。」書載薛蟠給寶釵一箱筆、墨、紙、硯、各色箋紙、香袋、香珠、扇子、扇墜、花粉、胭脂等物。外有「虎丘」帶來的自行人、酒令兒,水銀灌的打筋斗小小子,沙子燈,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,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。又有在「虎丘」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,與薛蟠毫無差錯。兩言虎丘巧是「同上虎邱」?寶釵將那些玩意兒一分一分配合妥當,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,賞賜來使,說見面再謝。是寫「群美之」。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,反自觸物傷情,想起父母雙亡,又無兄弟,寄居親戚家中,那裏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?想到這裏,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。這反是特寫「妒之」了。寶玉挨著黛玉坐下,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著細瞧,故意問這是什麼,叫什麼名字。那是什麼做的,這樣齊整。這是什麼,要他做什麼使用。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。像煞「與予指點舊遊」。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條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,是隱喻「重理前事」句。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,解了悲痛,可謂「吳門知姬者」。黛玉道:自家姊妹,這倒不必。只是到他那邊,薛大哥回來了,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迹兒,我去聽聽,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,則解作「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」。「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迹兒,」是「咸稱其俊識」。「只當回了家鄉一趟」是「得所歸」,把回鄉作歸鄉。
《庵憶》云:「謂姬何暇精細及此。」書載薛家夥計內中一個道:別是這麽著罷?衆人問怎麽樣,那人道: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,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。他原會些武藝,又有力量,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,特意跟他去,在背地擺佈他,也未可知。「那樣個伶俐人」寫「何暇精細」。「未必是真」寫「及此」。本處有《靖藏眉批》「似糊塗卻不糊塗,若非有風緣根基有之人,豈能有此□□□姣姣冊之副者也。」其中「不糊塗」為「精細」也。
《庵憶》云:「復遍覓之,」書載衆人問薛蟠: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?薛蟠說:城裏城外,那裏沒有找到?不怕你們笑話,我找不著他,還哭了一場呢。言畢,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,不像往日高興。「城裏城外,那裏沒有找到?」是「復遍覓之」,本處有《靖藏眉批》「獃兄也是有情之人。」作為標記顯然。
由以上五處作成比較,發覺有「普及本」中「黛玉道:自家姊妹,這倒不必。只是到他那邊,薛大哥回來了,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迹兒,我去聽聽,只當回了家鄉一趟的」一段文字與「戚序本」之記載「黛玉原不願意爲送這些東西來就特特的道謝去,不過一時見了,說一聲就完了。今被寶玉說得有理,難以推託,無可奈何只得同寶玉去了」異趣。後者頗不見容於《影梅庵憶語》「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」的解讀,知是以「普及本」為勝出。
意外運用《孟子、齊人章》假語村言解讀之下卻又另有發現。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,其良人出,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,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:良人出,則必饜酒肉而後反;問其與飲食者,盡富貴也,而未嘗有顯者來,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。蚤起,施從良人之所之,遍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閒,之祭者,乞其餘;不足,又顧而之他,此其為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告其妾曰:良人者,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。與其妾訕其良人,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,施施從外來,驕其妻妾。」這是眾所周知的故事。
作者套寫長篇大論是要分段來表達,掩人耳目。話說「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」,書中是以賈璉作齊人,剛好他有鳳姐、平兒的一妻一妾。三十九回有《批注》說「妙文!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,此則先見鳳姐後見平兒也。何錯綜巧妙得情得理之至耶?」呼應第六回中「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。」《批注》說「記清。」那才是姥姥見平兒之處,批書人特在點醒「處室」,也就是房室的區處之意。
二十一回載「那個賈璉,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,獨寢了兩夜,便十分難熬,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。」是寫「其良人出,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」。然後二十二回鳳姐問賈璉以寶釵生日怎麼作?是寫「其妻問所與飲食者」也。賈璉答話「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,這會子倒沒了主意?」含有玄機,此處是寫「則盡富貴也」,多大生日實寫「富貴」二字。
劉姥姥遊大觀園時,鳳姐與鴛鴦商議要拿他取個笑兒,是寫「其妻告其妾曰」。鴛鴦笑道:天天咱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篾片相公,拿他取笑兒,是以「外頭老爺們」寫「良人出」。姥姥逗笑,史湘雲噴飯,薛姨媽噴茶,失控場面是寫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」,把吃下去的東西都反出來了。劉姥姥誇鵪鶉蛋小巧,鳳姐兒說是一兩銀子一個,寫「問其與飲食者,盡富貴也」,富貴人家才吃得起。劉姥姥好不容易撮起一個蛋要吃,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,是寫「而未嘗」。劉姥姥歎息怪道說禮出大家,是寫「有顯者來」,大家是顯貴之家。姥姥失蹤,眾人尋找不見,襲人說我且瞧瞧去,是寫「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」。
四十六回載寶玉藏身山子石後,鴛鴦、襲人、襲人三人「唬了一跳」,是寫「蚤起」,跳蚤也。「看你低著頭過去了,進了院子就出來了,逢人就問。我在那裏好笑,只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,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,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。」是寫「施從良人之所之,遍國中無與立談者。」逢人就問,是「遍國中」,藏藏躲躲則是「無與立談者」,此處是把良人當成姨娘了。
賈敬死後停靈城外鐵檻寺裏,是寫「卒之東郭墦閒」,鐵檻寺本名饅頭庵,比擬土饅頭自有其道理在。賈璉因賈敬停靈在家,垂涎二尤,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,是「之祭者乞其餘」,賈珍是喪祭者。俞祿回說給銀仍欠六百零十兩,是寫「不足」。賈珍打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主意,賈蓉問過尤氏,說剩的三百兩交與老娘收了。這是寫「又顧而之他」,「顧」是尤氏,「之」是老娘。賈璉表態挪借銀兩,借機親近二姐以饜其欲,大開尊口是「此其為饜足之道也」,說得頭頭是道。解讀到此,接下去問題可就來了。鳳姐問完興兒話後,相對於「普及本」的簡略敘述「這裏鳳姐才和平兒說:你都聽見了?這才好呢。平兒也不敢答言,只好陪笑兒」不足以解讀「其妻歸告其妾曰:良人者,所仰望而終身也,今若此。與其妾訕其良人」而「戚序本」卻有下面這段文字供作解讀。
「且說鳳姐見興兒出去,回頭向平兒說:方纔興兒說的話,你都聽見了沒有?平兒說:我都聽見了。鳳姐說:天下那有這樣沒臉的男人!吃著碗裏,看著鍋裏。見一個,愛一個。真成了喂不飽的狗,實在的是個棄舊迎新壞貨。只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!他別想著俗語說的家花那有野花香的話,他要信了這個話,可就大錯了。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狠沒臉,親戚朋友見不得的事出來,他纔罷手呢!平兒在一旁勸道:奶奶生氣卻是該的。但奶奶的身子纔好了,也不可過於氣惱。看二爺自從鮑二的女人那一件事之後,到狠收了心,好了呢。如今爲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?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。」鳳姐回頭向平兒說話是「其妻歸告其妾曰」。「天下那有這樣沒臉的男人」寫「良人者」。「吃著碗裏,看著鍋裏」寫「所仰望」,鍋比碗要大。「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狠沒臉,親戚朋友見不得的事出來,他纔罷手」寫「而終身也」,早晚是時間,罷手是終了。平兒說「如今爲什麼又幹起這樣事來?這都是珍大爺他的不是」,寫「今若此」。鳳姐背地大罵賈璉是「與其妾訕其良人」,反觀「普及本」卻始終沒有責罵的話語。
接著第六十八回載二姐行禮,鳳姐下座還禮,口說願作妹子,容一席之地安身,死也願意。說著,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尤二姐見了這般,也不免滴下淚來,二人對見了禮,分序座下。是即「而相泣於中庭」,「庭」字通作「廷」解。等賈璉事畢回來,先到了新房中,已竟悄悄的封鎖,老頭子細說原委,賈璉只在鐙中跌足。是寫「而良人未之知也」。賈璉見了賈母和家中人,回來見鳳姐,未免臉上有些愧色。是「施施從外來」。誰知鳳姐兒他反不似往日容顔,同尤二姐一同出迎,敘了寒溫。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,未免臉上有些得意之色,驕矜之容。是寫「驕其妻妾」。
作者大費周章把《齊人篇》從頭到尾套寫完全,刻劃出身側福晉的「繼后那拉氏」一妻一妾公案,卻又意外地作為驗證六十七回的工具。而總上所得結果,不難窺知兩種版本各有優勝,不能有所取捨。唯有透過不斷的解讀判別,才能還《紅樓夢》以本來面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