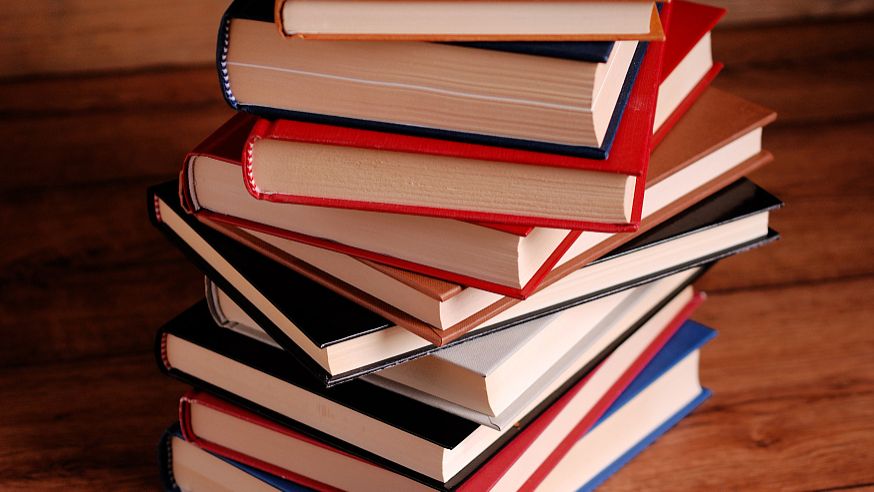雪地里隐隐传来猎狗的叫声。大雪决绝地封锁了一切,除了旅店窗户透出的暖黄色的灯光、以及屋顶升起的一线炊烟。
旅店内,则又是另一番景象:炉灶上正炖煮着肉汤,女侍把切好的卷心菜、胡萝卜、洋葱倒入了锅中,香气四溢。劳顿的旅客靠在暖炉边上,烘干冻透了的双手和靴子。
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高高的凳子上,她是个看上去并不和气的妇人,此刻正剖开鱼腹似的用小刀拉开信封,从中取出信件。
阿列克谢裹在毛毯里,浑身打了个哆嗦。他双眼无神地注视着壁炉,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——如若不细看,通常难以辨出那种被疲惫所消蚀、模糊后的惊恐。
“你有十五岁吗?”旅店老板问。
“先生,十六岁过了。”阿列克谢怯怯地答道,生怕出什么差错。
旅店老板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口气。“你就睡这儿可以吗?”他指了指炉边的一张床榻。尽管没有单独的房间,但至少看起来舒适而温暖。
阿列克谢的神情闪过一瞬的不自然,但接下来,他匆忙地道了谢,以他惯常用于应允的那副神情,轻易地答应下来。
老板替他弄了点热杜松子酒来,这种紫红色的药水对冻僵了身子的人最有好处。酒精让阿列克谢有点儿眩晕,他躺在火炉边上,耳畔隐约传来旅店内众人的谈话声。
“北方的强盗袭击了庄园?”
“不错,罗曼诺夫的府邸上,连条能叫唤的狗都不剩,全部被强盗们打死了。”
阿列克谢微不可查地把身子往被子里缩了缩。
“在那些被杀死的人中,失踪了一个仆人——说不定他和那些强盗是一伙?”
“这也难说,警察现在正在追查他的消息。不过,保不齐他们会让他做替罪羊。”
阿列克谢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他把怀里的东西往心腹的方向揣了揣,把头一偏,勉强入睡。
他睡得很浅,这丁点儿睡眠对他精神的补偿,不过像是搁浅的鱼依靠翕动鳃丝所获得的氧气那样甚微。期间,各种幽深、错杂的梦境不断折磨着他,让他濒临崩溃。
他梦见自己站在法庭上了,周遭是面目模糊的人群。面对陪审团,他哆哆嗦嗦地说不清一句话,只有不断地哭诉:“先生们、大人们!我是无辜的、我是无辜的呀!”
高处传来冷冷的笑声。随后,他们就传唤证人:有好几人报告说,曾目睹他慌不择路地逃离庄园,法庭上也摆出了那些从他身上搜出的证物——从血里割出来的价目。
一阵响动轻易地把阿列克谢惊醒了。
“得了,把它拿来给我,婆娘,别这么小气。”他听见一个男人说道。
随后传来女人不满的嘟囔声。
半梦半醒之间,一些苦涩的药水滴进他的嘴里,呛得他一阵猛烈地咳嗽。待一切平息后,他又再度闭上了眼。
旅店内,则又是另一番景象:炉灶上正炖煮着肉汤,女侍把切好的卷心菜、胡萝卜、洋葱倒入了锅中,香气四溢。劳顿的旅客靠在暖炉边上,烘干冻透了的双手和靴子。
老板娘坐在柜台后面高高的凳子上,她是个看上去并不和气的妇人,此刻正剖开鱼腹似的用小刀拉开信封,从中取出信件。
阿列克谢裹在毛毯里,浑身打了个哆嗦。他双眼无神地注视着壁炉,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——如若不细看,通常难以辨出那种被疲惫所消蚀、模糊后的惊恐。
“你有十五岁吗?”旅店老板问。
“先生,十六岁过了。”阿列克谢怯怯地答道,生怕出什么差错。
旅店老板微不可查地叹了一口气。“你就睡这儿可以吗?”他指了指炉边的一张床榻。尽管没有单独的房间,但至少看起来舒适而温暖。
阿列克谢的神情闪过一瞬的不自然,但接下来,他匆忙地道了谢,以他惯常用于应允的那副神情,轻易地答应下来。
老板替他弄了点热杜松子酒来,这种紫红色的药水对冻僵了身子的人最有好处。酒精让阿列克谢有点儿眩晕,他躺在火炉边上,耳畔隐约传来旅店内众人的谈话声。
“北方的强盗袭击了庄园?”
“不错,罗曼诺夫的府邸上,连条能叫唤的狗都不剩,全部被强盗们打死了。”
阿列克谢微不可查地把身子往被子里缩了缩。
“在那些被杀死的人中,失踪了一个仆人——说不定他和那些强盗是一伙?”
“这也难说,警察现在正在追查他的消息。不过,保不齐他们会让他做替罪羊。”
阿列克谢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他把怀里的东西往心腹的方向揣了揣,把头一偏,勉强入睡。
他睡得很浅,这丁点儿睡眠对他精神的补偿,不过像是搁浅的鱼依靠翕动鳃丝所获得的氧气那样甚微。期间,各种幽深、错杂的梦境不断折磨着他,让他濒临崩溃。
他梦见自己站在法庭上了,周遭是面目模糊的人群。面对陪审团,他哆哆嗦嗦地说不清一句话,只有不断地哭诉:“先生们、大人们!我是无辜的、我是无辜的呀!”
高处传来冷冷的笑声。随后,他们就传唤证人:有好几人报告说,曾目睹他慌不择路地逃离庄园,法庭上也摆出了那些从他身上搜出的证物——从血里割出来的价目。
一阵响动轻易地把阿列克谢惊醒了。
“得了,把它拿来给我,婆娘,别这么小气。”他听见一个男人说道。
随后传来女人不满的嘟囔声。
半梦半醒之间,一些苦涩的药水滴进他的嘴里,呛得他一阵猛烈地咳嗽。待一切平息后,他又再度闭上了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