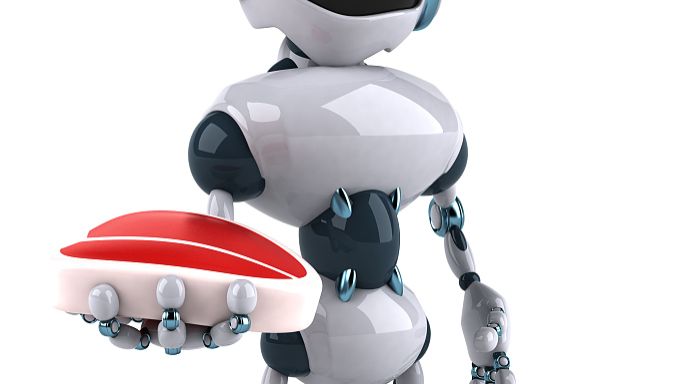【参演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。】
第19章
如果要找一个比大卫·芬恩更低俗、粗鄙的角色,恐怕得费一番功夫。如果像芬恩这样的人搬进你的社区,那无疑是房价暴跌的明确信号。他的脸上长满了毛发——与其说是胡子,不如说更像鸟巢——他穿着脏兮兮的运动鞋、保暖裤和睡裤四处晃荡;他的衣服上沾满了烟灰和早餐果酱的污渍。但如果说他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,他的行为则更糟糕,他是个口无遮拦的邋遢鬼。简而言之,他绝对是我想在电视上扮演的一切:与弗兰克·斯宾塞完全相反的角色。
是我在《没出息的孩子》的原导演迈克尔·米尔斯——现在是泰晤士电视台的制片人——在1979年的电视剧《粉笔与奶酪》中给了我大卫·芬恩这个角色。乔纳森·普赖斯曾在试播集中出演,但他选择不继续参与系列剧。我认为他在塑造大卫·芬恩这个角色时做得非常出色,所以我毫不羞耻地借鉴了他的一些表演风格。我非常享受扮演这个角色,尤其是因为我又能和迈克尔一起工作了。
我们一开始在收视率上排名第一,结束时大概排在第七,观众人数达到了1800万:这已经非常不错了,但按照我们以往的标准,这并不算大获成功。
我不知道谁更讨厌大卫·芬恩这个角色——是迈克尔·克劳福德的粉丝(或者我该说弗兰克·斯宾塞的粉丝?)还是我的祖母。她总是忠诚地在剧集播出时打开电视,但她坚决拒绝看屏幕,而是背对着电视机坐着。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,我还收到了数百封投诉信,抱怨我扮演这样的角色。如果乔纳森·普赖斯来演这个角色,他们可能会很喜欢。但“我们的迈克尔”不行。“我们更愿意看他演弗兰克……”我不想再听这些了。迈克尔·米尔斯很想再拍一季——当然比我同意拍的八集要多——但我拒绝了,突然之间,另一件看起来更重要的事情出现了。
有时候,当一个演员非常幸运时,他会读到一个剧本或听到一首歌,然后他会知道自己的名字与它紧密相连——他知道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。我刚刚收到了一部名为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的剧本和音乐磁带。这部剧讲述了一个智力障碍的男子参与科学实验,成为天才并爱上了他的治疗师,最终却发现他将再次退化,永远回到他以前的状态。智力障碍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题材,但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它,在我看来是非常勇敢和大胆的。丹尼尔·凯斯的小说已经成为一种经典,电影版《查理》让主演克里夫·罗伯逊赢得了奥斯卡奖,所以这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。
顺便说一下,标题中的“阿尔吉侬”是查理最好的朋友,一只老鼠。我和一只老鼠一起训练和工作了几个月——它非常聪明,是个真正的明星。我们甚至一起表演了一段歌舞杂耍,它会一路跑到我的手臂上,坐在我的头上,或者从一只手臂跑到我的肩膀,再从另一侧跑下来。然后我会把它放在地上,大步走下舞台,而阿尔吉侬则紧紧跟在我后面。我们的小表演总是能让观众捧腹大笑。我把老鼠(还有它的两个替身)放在我的化妆室里。我那长期受苦的服装师凯特·阿伦斯讨厌老鼠,而我总是让它们在我的肩膀上爬来爬去,或者在排练时在化妆室里弄丢一只,这让她抓狂。
当我听到查尔斯·斯特劳斯那简洁而美妙的配乐时,我就知道这是为我准备的。我被深深吸引住了;我甚至还没听完磁带,就已经在脑海中扮演查理,并思考如何进一步与这个角色产生共鸣。音乐、故事,这部剧的一切都深深打动了我,并激发了我的灵感。我想我从未对一个项目有过如此迅速的反应。
我当然知道查尔斯·斯特劳斯,这位多产、热情的美国人,拥有无数百老汇和西区的热门剧目。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与他的《再见,小鸟》或《安妮》截然不同。查尔斯实际上将其描述为一种室内音乐剧——可能在演员和乐队的规模上较小,但它依然是一部强大的作品。
乔安妮和我一样喜欢这部剧,我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的项目,这是我们自从在《比利》中成为舞伴以来一直想做的事情。(她后来在剧中跳舞,并协助编舞师罗达·莱文。)
英国导演彼得·科——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——给我寄来了剧本。彼得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他执导的《奥利弗!》,当时他是加拿大埃德蒙顿城堡剧院的艺术总监,刚刚执导了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。我们安排尽早见面,在排练之前,从一开始就很清楚,未来可能会有火花。彼得和我在戏剧上截然不同;如果我们是有意为之,我们也不可能更不同了。
彼得有时在态度上会显得咄咄逼人,非常傲慢。但他也非常聪明、老练、有文化(我敢肯定他读过的书比我多得多),举止略带贵族气质,是一个复杂而冷静的人。有一段时间,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张。我们俩都可能在言语上好斗,我们早早地就划定了自己的哲学立场。例如,每当我和任何人讨论一部作品时,我都会频繁使用“我们”这个词;我喜欢在一个团队中工作,作为团队的一部分。然而,彼得对“我们”这个概念并不像我那么强烈。
从一开始,我就坚持至少在选角方面要有一定程度的协商。彼得的观点是,选角是他的事,与我无关。“好吧,如果这是你的工作方式,”我对他发火道,“如果你想不经过协商就做……”然后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剧组,几天后,彼得打来了一通和解电话,向我保证我们确实可以一起工作,他会同意一定程度的协商。(他承诺的是一定程度,而我得到的也正是一定程度——我觉得他从未真正让我感到被压倒。)
有一段时间,排练就像某种原始的领地舞蹈:我的手指在他鼻子下挥舞,他的手指在我鼻子下挥舞,我们俩都大喊:“就这样!就这么定了!”然后我们会朝相反的方向走开,停顿一下,再转身面对彼此,其中一个人会说:“当然,如果你愿意……”然后我们就会大笑起来。两个非常不同的人,走完全不同的路,试图达到同一个共同的目标——尽可能制作出最好的作品。
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表演者,情感外露,充满激情,情绪高涨。而且很容易流泪:我在课堂上唱一首悲伤的歌时都会哭。彼得则完全相反;他从不表露任何情感。他会面无表情地坐着看我,眯着眼睛全神贯注。他留着胡子,习惯性地咬着下唇,那种狂热让我几乎相信周围的黑色胡须一定尝起来像甜甘草。我在表演中投入的情感越多,他就越用力地咬着“甘草”,尤其是在剧中查理意识到自己再次退回到那种噩梦般的孩童状态时——他知道自己正在逐渐失去理智,而他对此感到厌恶。
“……我不会回去,不会在这个阶段
回到黑暗,回到那个笼子里。我会找到一种方式留下来
查理,查理,查理……”
我对查理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,当我以一种角色与演员的奇怪结合唱出这些歌词时,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了自己之外。我成了自己的观众,看着这个男人,为他加油,每次排练这首歌时我都会流泪。
“是什么让你在那里哭?”彼得问。
“我不知道,”我说,“这不是自怜……这是一种感觉,我不会回去,我不能回去……这是挫败感,愤怒。”
“再试一次,”他说,“这次要克制,把情感拉回来,远远地拉回来,然后再释放……”这就像一种情感弹弓。他鼓励我探索和审视歌词中的关键词语和短语,并敦促我以这些歌词为基础,真实地表达情感。彼得教会了我如何将一首歌剥离到其最本质的歌词,构建和发展情感内容,直到它成为角色的延伸。他让我明白,只要我在这过程中正确地构建了角色,并为观众做好了准备,那么在歌曲的背景下,情感可以走向任何极端——事实上,可以走向巅峰。观众会接受你在演唱时设定的所有情感高度。你不能只是站在舞台上哭泣,然后期望观众也跟着哭。
在为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做准备时,我参观了疗养院,不是像过去那样作为表演者,而是作为观察者。我在某处读到,我们从未真正表演真相,我们只是反映它,诠释并修饰它。在我看来,最重要的事情是以应有的尊严对待智障这一主题。我不想让查理的天真被讽刺所贬低。每当我参观这些设施时,我都会想起温柔的萨姆,他是我在贝克斯利希思时大卫·格里格商店的清洁工。他非常像查理,尽管与查理不同,萨姆有他的独立性,有他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自尊——这些东西在机构的围墙内很容易丧失。我在后台有一个小角落,每次演出前我都会去那里,思考这个男人,以及构成他世界的天真和纯真。在那个角落里,生活似乎变得缓慢而简单——有人会叫我的名字,我会转过身,突然变成那个成年孩童查理。
有两位非常有才华的演员扮演查理的医生:奥布里·伍兹,饰演咄咄逼人、严肃的斯特劳斯博士,以及拉尔夫·诺塞克,饰演更温和的尼穆尔博士。拉尔夫的声音非常温柔,当我扮演查理时,我爱他。每当拉尔夫在舞台上对我说话时,我都觉得他可能是我的父亲或某个叔叔。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妙的小场景,尼穆尔博士让查理接受罗夏墨迹测试。我总是想通过测试来取悦拉尔夫。
我想特别提到另一位对我来说非常特别的女主角。有几位女演员因为我们的合作关系而让我特别珍惜:就像一位优秀的网球搭档,她们每个人都让我更加努力。米歇尔·多特里斯是其中之一,而我在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中的搭档谢丽尔·肯尼迪是另一位。
谢丽尔和我一样,在听了音乐磁带的一小部分后就爱上了这部剧。她的冷静和自信多次拯救了我。就在首场预演之前,决定让我唱《无论有多少时间》,这首原本由谢丽尔独唱的情歌。我完全不知道歌词,只好把它们写下来,放在谢丽尔头后的侧幕里,这充其量是一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,而且是我从与哈里·科贝特在《旅行之光》中的疯狂日子里学到的要避免的做法。这次我完全失算了:侧幕里太暗了,我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在完全恐慌之前,谢丽尔拉着我的手,轻轻地把歌词念给我听,温柔地引导我唱完这首歌。她对我以及整个剧组都有着非常镇定的影响。
《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》于1979年6月19日在女王剧院首演,评论家们意见不一。那些喜欢这部剧的人非常喜爱它,并给了我一些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评价。那些不喜欢它的人大多是因为题材而感到不适。
南当然也来看演出,尽管她的视力已经非常差了。我确保她坐在前排,但即便如此,我怀疑这部剧对她来说是否只是一个彩色的模糊画面。不过,她的听力非常敏锐。在第一幕中,当查理从白痴变成天才的旅程开始时,他的进步通过他唱的几本书来表现,从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开始,到更具挑战性的《化身博士》(“这很好,但太简单了”),最后以《战争与和平》的快速解说结束(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丹尼·凯伊那复杂而精彩的快板):
安德烈去打仗,丽莎死了,但留下了一个儿子。
尼古拉也在战斗,他们在对抗拿破仑。
皮埃尔的妻子叫艾伦,她是瓦西里亲王的女儿;
皮埃尔本要去打仗,但他解放了他的农奴。
我是不是忘了提到安德烈还有一个妹妹,艾伦有一个弟弟,还是这对你来说太多了?
当安德烈遇到娜塔莎时,他全心全意地爱她,但她遇到了艾伦的弟弟,他是个混蛋——那就是阿纳托尔……
我把这首歌的最后一个音符拉得尽可能长。最后,我不得不转向谢丽尔饰演的角色,气喘吁吁地说:“我做得怎么样?”
在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之前,前排传来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:“你做得太棒了,亲爱的。”那是南。
我简直要晕倒了。哦,天哪,我简直不敢相信!
“你做到了——你真的做到了!”她坚持道。
谢丽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她眼里含着笑出的泪水,盯着我,努力不让自己完全崩溃——直到我也开始笑起来。后来南告诉我她有多喜欢这部剧。“但它不会持续太久,你知道的,”她说,“它不会持续太久。”
“南!”我说,“我刚得到了一些我职业生涯中最好的评价!”
“我知道你有,亲爱的,你太棒了。但它不会持续太久。”
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:她说这话很奇怪。她怎么会知道?她甚至看不到这部剧。
这部剧,包括预演,只持续了六周。当它结束时,她说:“我就知道它不会持续太久。我就知道它不会持续太久!”
“南——!”